不久前一位同行向年轻人介绍我,说我以紫杉醇研究而出名。姑且不说这个所谓名气价值几许,事实上我确实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接触紫杉醇,此后花了十几年时间一直研究紫杉醇及其类似物,科研产出也多与此相关(除了另外两个靶点相对少量的工作,参见),所以被贴上“紫杉醇研究者”的标签也不意外。
那就从紫杉醇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紫杉醇(化学结构属于紫杉烷类)是一种抗微管药物,或者说作用于微管的分子(microtubule targeting/associated agent, MTA)。这类药物中在临床上应用的有:长春碱类(vinca alkaloid)4种和紫杉烷类(taxane)分子3种,还有与紫杉烷作用类似的埃坡霉素类(epothilone)1种,都是用于治疗癌症的。只不过长春碱类主要针对血液系统(非实体瘤),而紫杉烷和埃坡霉素针对实体瘤。还有一个美登木素(maytansine)衍生物DM1的抗体偶联物,用于肿瘤治疗。此外,还有秋水仙碱(colchicine),可用于治疗痛风。
早期的细胞毒类抗癌药如DNA烷化剂等,被认为主要针对快速生长和分裂的肿瘤细胞(正常细胞繁殖速度较慢,被破坏较少)。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虽能杀伤癌细胞,但对于同样快速生长和分裂的正常细胞(如骨髓、消化道和毛囊细胞等)也毫不留情,或者说缺乏选择性。这也是为什么细胞毒类抗癌药大多具有骨髓抑制、消化道损伤和脱发等毒副作用的原因。
在白血病这类细胞繁殖速度*快的癌症治疗中,长春碱类MTA对肿瘤和正常细胞的区分仍旧沿袭了这个套路。不过要解释MTA的实体瘤治疗作用麻烦就来了:某些肿瘤特别是实体瘤对紫杉烷类MTA敏感,但肿瘤生长速度却很缓慢。按上述道理去推断,这类MTA对骨髓的损伤恐怕大于肿瘤,然而临床效果却并非如此。虽然MTA也有相当大的毒副作用,包括骨髓抑制、手脚麻木(对外周神经系统的毒性)等,但它们在有效剂量范围内确实能有效杀伤肿瘤。这就是所谓的繁殖速度悖论(proliferation rate paradox)。
哈佛医学院的Mitchison尝试对这个谜题做出回答。他发现紫杉醇对动物体内肿瘤组织中细胞的杀灭,与对培养基中肿瘤细胞的杀灭颇为不同。动物体内仅有不到1/4与对培养基中肿瘤细胞的杀灭方式类似。基于他自己和其他实验室的有关结果,提出可能有4种MTA经典作用之外的途径[1]:
(1)在实体瘤中蓄积
已知紫杉醇在胞内比胞外浓度可高出几十倍,通过蓄积可提高抗癌作用(与靶向给药能起到类似作用)。但紫杉烷为什么能蓄积?已知某些化合物能够在肿瘤中蓄积(例如卟啉类分子的蓄积,与肿瘤经无氧代谢产生的微酸环境有关),这种蓄积也可能与转运蛋白(transporter)的功能有关。不过,紫杉醇是外排蛋白Pgp的底物,应该是容易被排出而非蓄积。那么其理化性质如何影响在肿瘤细胞中的蓄积,难以理解。
除偶然发现某种化合物的肿瘤蓄积作用之外,如何进行系统研究?怎么预测化合物能在肿瘤组织中蓄积?这类研究或许可以帮助提高细胞毒药物的选择性。
(2)杀灭静止(肿瘤)细胞
临床相关剂量下的紫杉醇只能杀伤有丝分裂期的癌细胞,而对静止期肿瘤细胞杀伤,有可能是通过影响的肿瘤微环境而产生的,也可能与某些肿瘤细胞更容易受细胞凋亡影响有关。有人提出mitochondrial priming方法[2],可以帮助在临床上更有效地进行化疗。
对于MTA而言,肿瘤组织和正常细胞中的微管系统有何不同?有丝分裂期(MTA敏感)细胞和静止期细胞(也许还包括肿瘤干细胞)的微管系统有何不同?文献中对此较少关注。究竟是没人觉得重要,还是无从下手?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无疑有助于发展选择性更高的MTA。
(3)杀伤其他非肿瘤细胞
对内皮、基质等与肿瘤微环境有关成分的作用,可能有助于整体的抗癌作用,也可能解释MTA的抗血管生成作用的来源,以及部分化合物对肿瘤转移的作用。MTA对白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免疫分子也有作用,但似乎更为复杂;不仅对抗癌有帮助,也可能会“帮倒忙”[3]。
以我自己对紫杉醇的结构修饰为例,尽管可以提高对肿瘤细胞的细胞毒和在整体动物水平上的抗癌作用,但也发现相应地提高了对免疫细胞(如T细胞)的细胞毒。这明显是人们所不乐见的,但如何消除这种无区分的作用尚不清楚。
(4)“旁观者杀伤”(bystander killing)效应
旁观者效应在肿瘤放疗中的作用已为人所知,也就是杀伤的(有丝分裂期)肿瘤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可以导致周围细胞的损伤或杀灭。这一效应让人兴奋之处在于,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可以通过正向反馈被不断放大(对此的实验证据支持还不够充分)。有人提出细胞毒药物通过immunogenic cell death也许是其*有效的作用方式[4],不过现实中抗癌药物能否达到这种效果尚不清楚。
本世纪初以来以激酶抑制剂为代表的分子靶向抗癌药物逐渐在业界被广泛接受,加之PD-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系统药物在近年兴起,包括MTA在内的细胞毒类药物遇冷并不奇怪。不过,且不说激酶抑制剂和免疫系统药物仍有自身问题需要解决,细胞毒药物也仍能通过提高对肿瘤的选择性得以发展。例如,以作用于DNA的药物为例,通过靶向表观遗传有关途径(如HDACi)就大大提高了选择性。对于比DNA作用药物更具选择性的MTA,也应通过增加基础研究,找到提高其对肿瘤作用选择性的方式。如何利用抗微管药物的多靶作用(特别是实现针对特定靶点产生所需要的作用),应是在此过程中值得探索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T. J.Mitchison. Mol Biol Cell 2012, 23:1-6.
2. T.Chonghalie et al. Science 2011, 334:1129-1133.
3. A. Javeed et al. Eur J Pharm Sci 2009, 38: 283-90.
4. O. Kepp et al. Cancer Metastasis Rev 2011, 30:61-69.



 1stDB4403/T 122-2020 人源肿瘤细胞系建立技术规范 现行
1stDB4403/T 122-2020 人源肿瘤细胞系建立技术规范 现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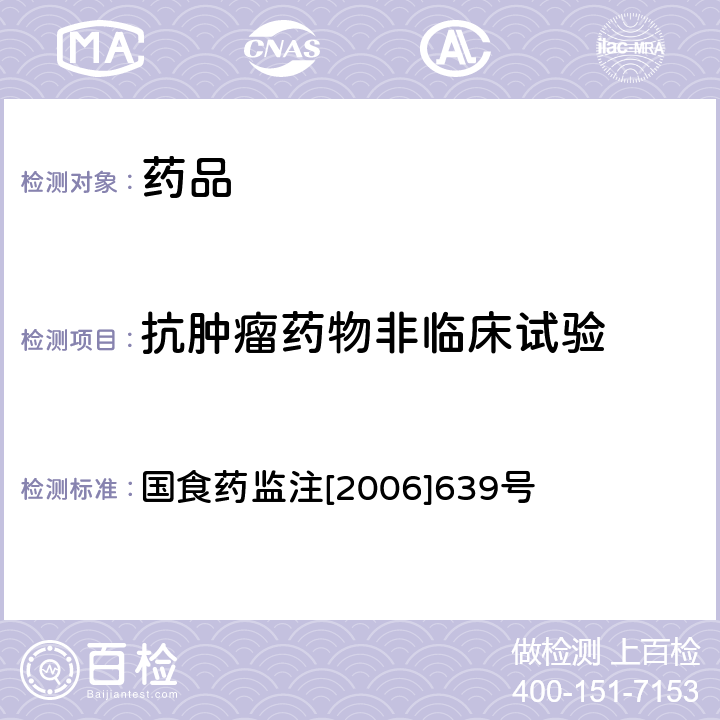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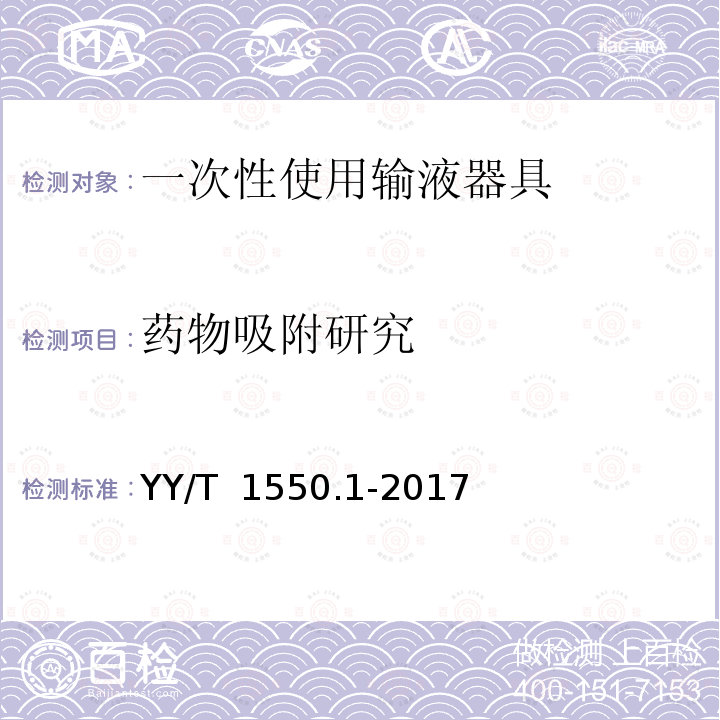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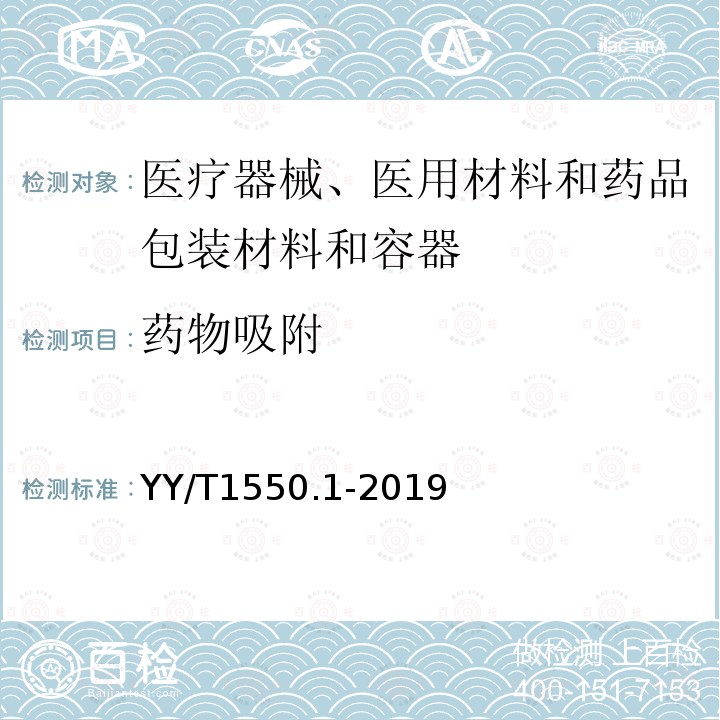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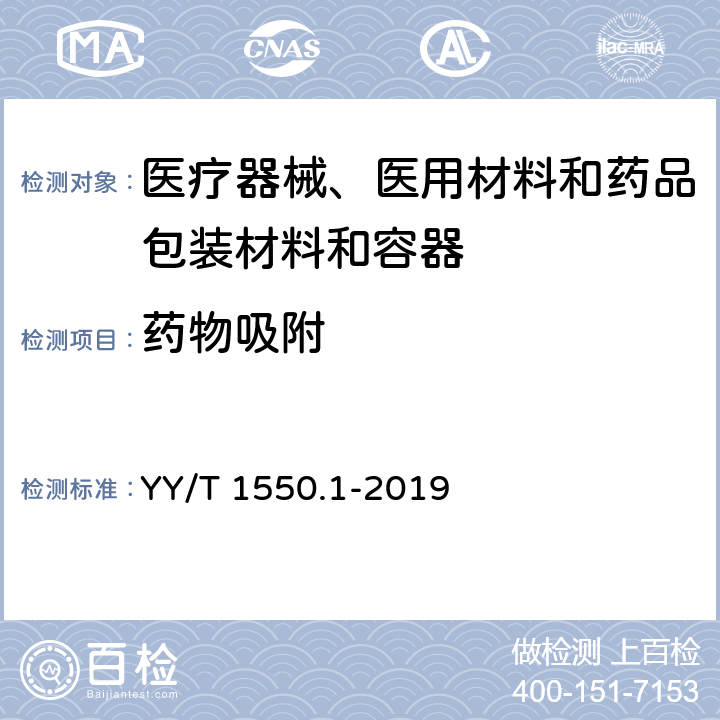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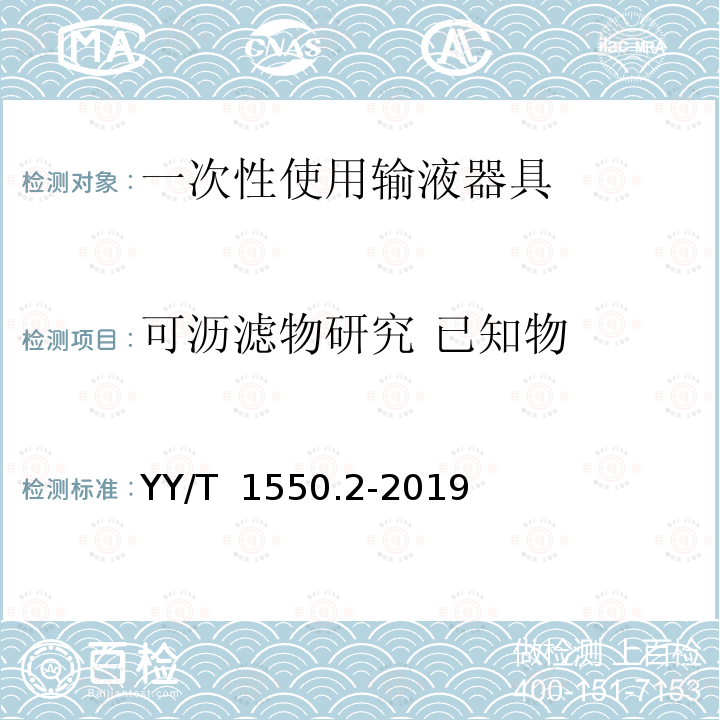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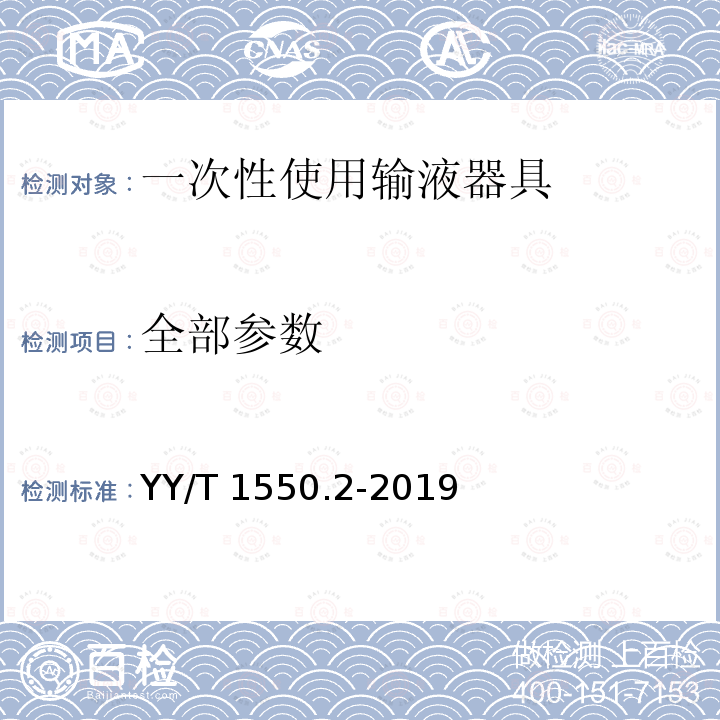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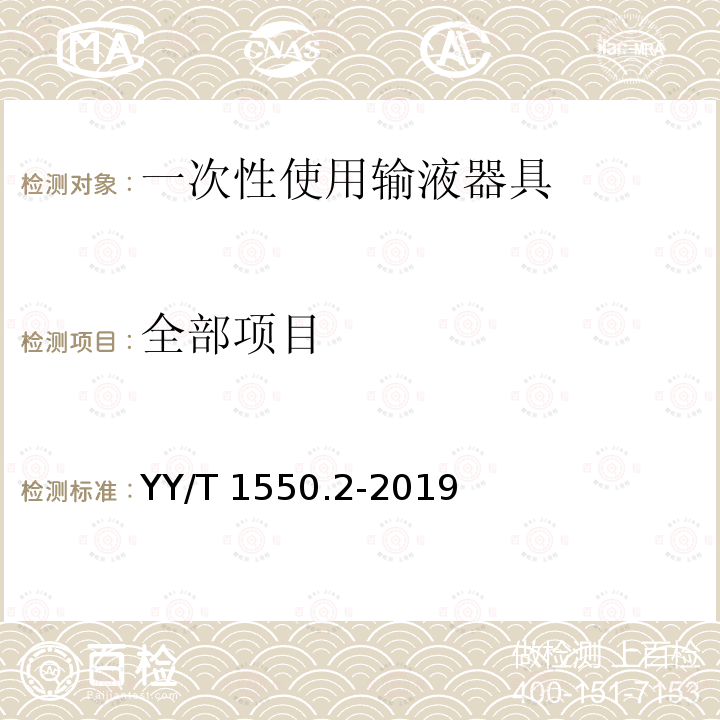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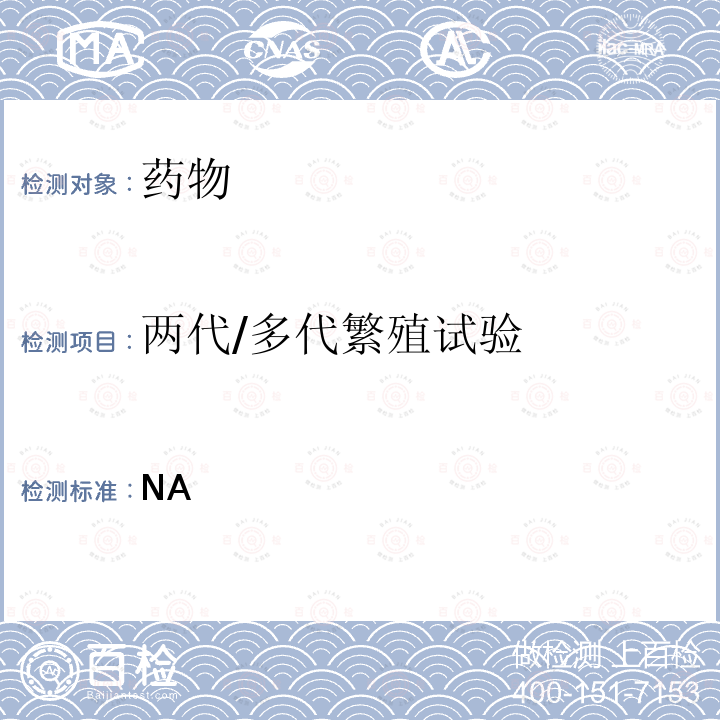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