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民族,在很长时期内以从事游牧业为主,随着种植业成分的不断增长,近代形成了并存的多种经济。
元代以前 蒙古人的直系祖先是东胡人的后裔之一的室韦人。南北朝隋唐时期,室韦人居住在今姚儿河以北,东起嫩江,西到呼伦贝尔的广大地区。契丹人称之为鞑靼。他们已有比较原始的农牧业,种植粟麦和穄,饲养猪、狗、牛,有少量马,没有羊。狩猎在经济生活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北部的室韦人。室韦人中有一个活动在额尔古纳河(古称望建河)的叫“蒙兀”的部落,后来成为蒙古各部的统一者,蒙古的族称亦渊源于此。
9世纪中期,长期雄踞蒙古草原的突厥败亡,回鹘西迁,大批室韦—鞑靼人乘虚涌入大漠南北,逐渐与留居该地的突厥语族居民相融合,其经济生活亦受突厥人影响,适应草原条件而转向以游牧为主。12世纪,这部分人子孙繁衍,形成许多部落集团。其中多数为草原游牧民,饲养马牛羊和少量骆驼,羊肉是主要的食粮,马是他们作战和游牧的主要工具,马乳发酵而成的马奶酒——“湩”是主要饮料。他们“逐水草放牧”。夏日暖和,聚牧于高山草场;冬季寒冷,移牧于向阳背风的山谷。各部落、氏族牧地有一定范围,蒙古语称为“农土”。还注意选配种畜,牧马除保留强壮的作种马外,余皆骟割。实行分群放牧,专人管理。游牧离不开毡帐和车子。屯宿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分布于圈内,称“古列延”。游牧又往往与游猎相结合,主要工具是弓箭,猎物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重要补充。种植业经济成分依然存在,如邻近中原的汪古等部“能种秫穄”,食粳稻;远在漠北的篾儿乞部也经营种植业。但种植业在蒙古人的整个经济中比重甚小。简单武器和生活用品一般由个体家庭自己制造,但也有专业的铁匠和木匠。蒙古各部还常用牛、羊、马、驼等与契丹交易,或作贡品。在草原北边森林地带的蒙古人则仍以狩猎为生,辅以捕鱼和采集。尚无畜牧业,唯养驯鹿作为游猎的运载工具。他们被称为“林木中的百姓”。
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出现部落贵族(那颜)、牧民(哈剌抽)和奴隶(孛斡勒)等阶级与阶层。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各部贵族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战争。在这过程中,蒙古孛儿只斤部贵族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国。草原各部落遂逐渐形成为使用共同语言的蒙古族。
元代
元代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通过镇戍或出仕足迹遍及全国,但主要仍聚居于漠北(岭北纡省)和漠南。蒙古统一漠北以至元朝建立,蒙古各部混战停止,出现相对稳定局面,又可以得到国家政权的大力扶持,蒙古族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元代漠北蒙古族人口有了成倍增长,这既以畜牧业发展为基础,又对畜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早在元朝建立前,窝阔台就指令每千户选派专人管理牧场的分配。为了开辟新牧场,又派人到一些缺水的地方打井,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也派兵到漠北浚井。国家还颁布了保护牧场的严格禁令,凡草生时掘地和遗火烧毁牧场者,要全家受诛。并禁杀羔羊、牝羊,以利牲畜繁育。元朝在从漠北到云贵的广大地区,选取水草丰美处设十四官马道,生产设备和牲畜饲料由地方政府无偿供应。如漠南地区的官牧牲畜,由政府提供人力物资,普遍盖搭棚圈,又推广牧草种植。大都留守司有专门的苜蓿园,并要求各村社“布种苜蓿”。这些措施使单纯的游牧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如蒙古人从被征服的西夏人那里学到了饲养骆驼的新技术,原来盛产于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善于养马和制作黑马奶的钦察人被选拔为皇室牧场的牧人和管理畜牧的官员。蒙古贵族畜群规模很大,从残存记载看,在皇室的个别牧场上,官有母羊即达30万头。一般牧民畜群亦颇可观,凡马、驼不够20匹,羊不足50只的,即被视为贫困户。蒙古国建立后,围猎已成为大汗和各级那颜喜好举行的带有军事演习性质的娱乐活动。但唐麓山以北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林中老百姓,仍主要以狩猎为主,而近水地区的牧民往往兼事渔捞,或以“耕钓为业”。元朝蒙古族经济中的种植业成分有了显著的增长,中原农耕文化有向蒙古族聚居区扩展之势,13世纪初,弘吉剌部聚居地区已形成以耕钓为业的聚落,该地后设应昌府(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经棚县),每年余储粮食近1万石。砂井、净州(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境)至延安府境的汪古人多从事农业,被称为“种田的白达达”。相传元代汪古部文学家马祖常的上祖即居净州,“自力耕垦”,成为富户。以前主要从事畜牧业的砂井等地的汪古人,也参加了农耕的行列。元人刘秉忠过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时,看到了“出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黎稠”的景象。在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土著的唐兀人也从事农业,开渠灌溉。在考古发掘中,内蒙古元集宁路遗址、凉城县游泥滩元代古城、固阳县葛舍沟、卓资县入苏木等地,都出土了元代的铁犁铧、铁齿耙、铁锢钩和磨盘、碌碡、杵臼等。在以前几乎没有农业的漠北,军事屯田有很大发展。成吉思汗时,即曾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忽必烈统一全国过程中及以后,加强对漠北地区的开发,政府多次派遣军队、调拨农具、耕牛、种子,在漠北各地屯田积谷。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和称海是当时漠北两大屯田中心。元成宗大德末年,哈剌哈孙受命办理称海屯田,疏流古渠,教部落耕作灌溉田亩数千顷,收米20余万石。漠北屯田主要劳动力是汉军,但也有蒙古人,如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命主要由蒙古人组成的拔都军在克鲁伦河域开渠屯耕。至于散居在内地的蒙古人,也有不少“种田户”。
明代
元亡以后,相当一部分蒙古人留居冀、豫、晋、陕、甘、滇等地,从事农业生产,与汉人的差别逐渐消失。退居蒙古草原的蒙古各部封建主则处于长期内讧中,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都受到严重破坏,许多被开垦的农田变得荒芜了,粗放的游牧经济又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蒙古族人民在十分困难和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了生产,赢得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明代中后期,蒙古族的畜牧业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如土默特部的封建主俺答汗有马40万匹,骆驼、牛、羊以百万数,其他一些大封建主也有几十万头牲畜。在明代的边镇马市上,蒙古族以大量牲畜和畜产品换取汉族的农产品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蒙古族经济中的种植业成分,在明代中后期也重新获得增长。各部封建主通过互市从中原输进农具、谷种、耕牛,发展其垦殖业。土默特旗的俺答汗亲自“用牛二犋,耕田约五六顷”,种植谷、黍、蜀秫、糜子。在其影响下,阴山以南出现“良田万顷”、“连村数百”的景象。白莲教首领丘富、赵全等,纷纷前往丰州建立城堡,“造屋力农”。其中“大板升”*大,城内蒙汉杂居,达五六万众。至16世纪末,汉族人口上升至10万左右。大量汉人的流入促进了土默特部农业发展,出现“腴田沃壤,千里郁苍”的局面。但因战争频仍,生产粗放,多无水利设施,只知犁地耙地,春种秋敛,既不锄薅,又不施肥,广种薄收。与此同时,位于蒙古草原东部的兀良哈三卫的农业也有相应进步。他们经常从中原购买犁铧农具和种子,并吸收先进耕作技术。史称其“可以耕稼,比之北虏,势实不同”。但生产方式仍*粗放,春耕时聚人马于平野,使之践踏粪秽后,播黍粟蜀秫诸种,即待收割。
清代
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前后,化了一个半世纪时间征服了蒙古各部,抑制了封建割据与战争,并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内地与草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使蒙古族社会获得了200年的稳定,对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同时,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活跃。尤其是随着国内人口激增,大批汉人进入传统的牧区,促使蒙古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纯游牧经济为多种经济结构所取代。
清初,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划地建旗,促进了牧地固定化和生产有序化,畜牧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获得改进。清中叶,半农半牧区牧业普遍实行打井,搭棚,筑圈,开辟“草甸子”,贮备冬饲料,饲养新役畜——驴、骡。接近农区半农半牧区的牧业也有明显进步。随着蒙古族畜牧业的持续稳定上升,牲畜头数大量增加。乾隆二十五年(1760)仅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岗崖两牧场就有大小牲畜50多万头。大批牲畜和畜产品投入了国内市场。
清代蒙古经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种植业成分的增长,改变了蒙古地区单纯游牧经济的面貌,农业(种植业)正式作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出现,并在传统牧区中形成了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农业的发展尤以喀拉喀和漠南蒙古各部*为突出。
清初,喀拉喀人的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等地,漠南蒙古的土默特、喀喇沁、察哈尔和归化城等地,农业都有一定发展,但耕作技术落后,种植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自17世纪末起,随着中原汉人大量流入及清政府在直辖领区实行放垦政策,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部分蒙古王公也实行放垦,蒙古族人民则逐步走向半农半牧,或定居,过着住土房、种植莜麦、糜子、黍、麦、豆、葱等农作物的生活。据乾隆八年(1743)统计,归化城土默特两旗蒙古人共有土地7.51万顷,其中牧地只有1.43万顷,占1/5弱。康熙在描述热河情况时说:“蒙古贫佃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鉴于放垦办法会对清廷在蒙古地区统治带来不良影响,乾隆四十年下令以重罚严禁蒙古各部继续向汉族人民放垦,嘉庆、道光时又一再加以重申。可是,随着清王朝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涌入蒙古地区的汉族流民实际有增无已,垦辟耕地不断扩大。至清后期,喀喇沁、土默特、察哈尔、归化城、伊克昭盟、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三旗、郭尔罗斯两旗等的农业生产规模都有惊人的发展。此外,乌兰察布盟所属四子王部落、达尔罕茂明安和乌拉特前、中、后等旗,也都产生了农业。到清末,在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农业已上升为主要地位,而蒙古“边近诸旗”,亦“渐染汉俗”。凡置郡县的地区,大体都以农业为主体。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部分蒙古族牧民学会了耕作技术,同时也使蒙古社会内出现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土地占有者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或将其租给揽头、商人、地主,并由其转租给汉族农民。农民向揽头交租,揽头又将地租一部分交给蒙古族土地占有者。实物地租是*基本的地租形态,每顷土地租粮一般为3~5石,还有定额的猪肉、粳米、白面、草料、柴薪等。租佃关系外,又有雇佣关系。佐领、参领以及其他蒙古族上层,实际上是与汉族地主相同的封建势力,而广大蒙古族人民则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底层。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后才彻底改变。
长期居于阿尔泰山和天山北路间的卫拉特蒙古人,元代时虽已习知农业,但因长期战乱生产发展缓慢。17世纪初,准噶尔部长巴图尔珲台吉崛起,他积*倡导利用从天山南路和中亚地区掠夺来的战俘从事耕作,又从西伯利亚引进种猪、种鸡。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辉特各部相继效尤,使农业在卫拉特蒙古各部广泛发展。巴图尔珲台吉死后,其继承人继续实行发展农业的政策,不但让俘获的维吾尔人、汉人耕种,也鼓励牧民从事农耕,额尔齐斯河流域、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成为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些人半农半牧,有些人则走向定居。卫拉特人的农业仍很粗放,春种秋敛,不粪不薅,广种薄收,但一般都要引水灌溉。耕地与牧地相距较远的富户,收获时还令人带鸟枪“看田打牲”。在阿尔泰地区,有的还在田中立“草人”或“木偶”以防鸟害。作物除黍、糜、大麦、小麦、南瓜、西瓜、葡萄外,还有少量蔬菜。



 1stDB15/T 1066-2016 蒙古族民俗礼仪 分类 现行
1stDB15/T 1066-2016 蒙古族民俗礼仪 分类 现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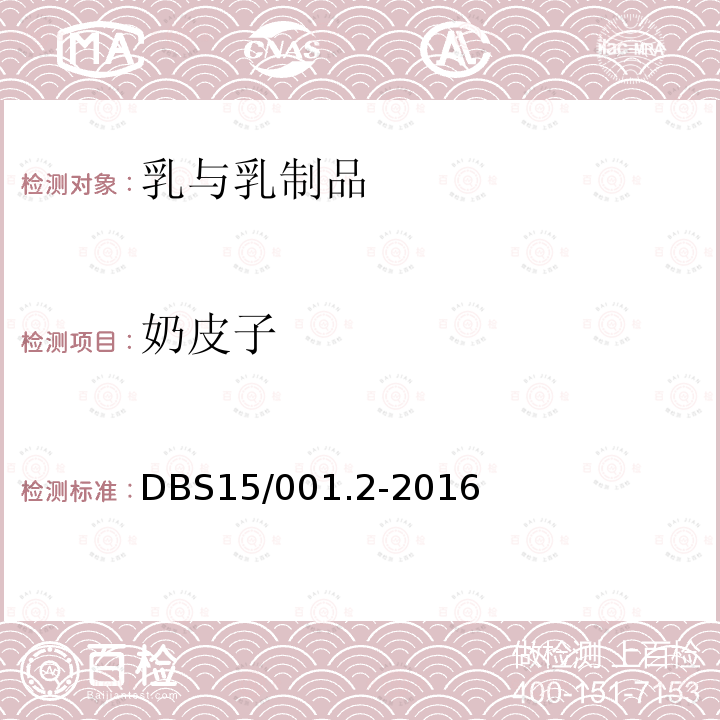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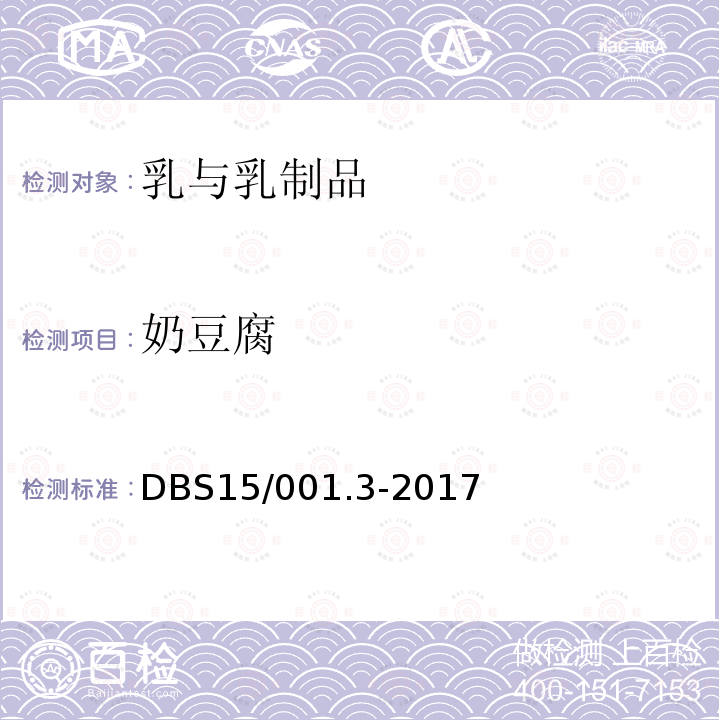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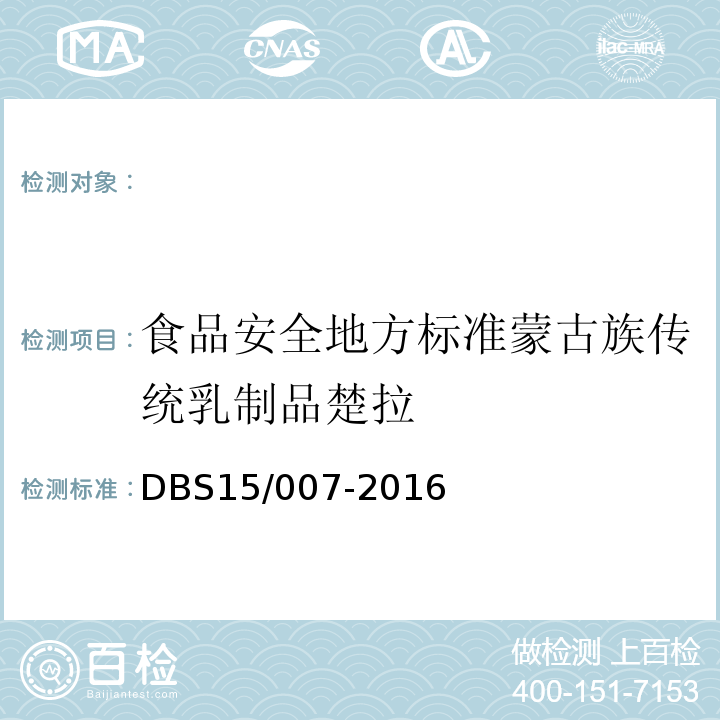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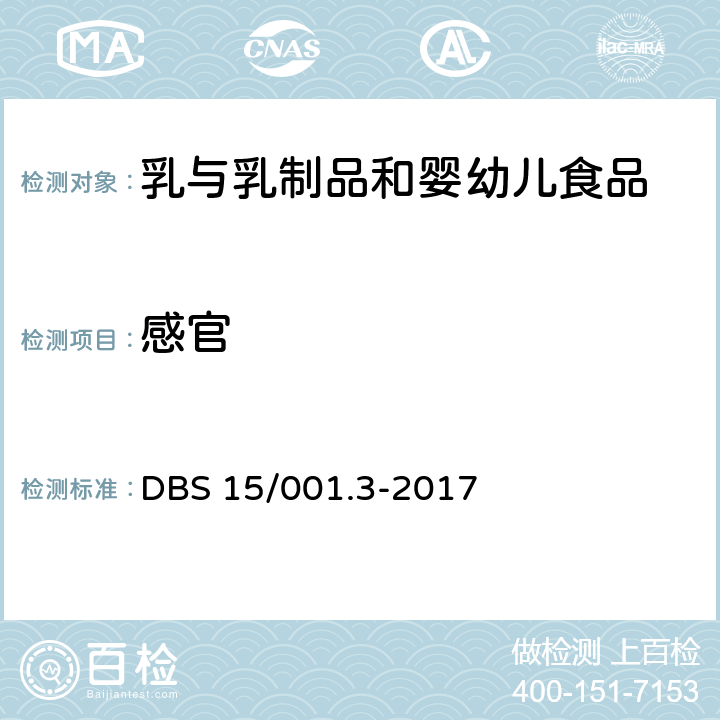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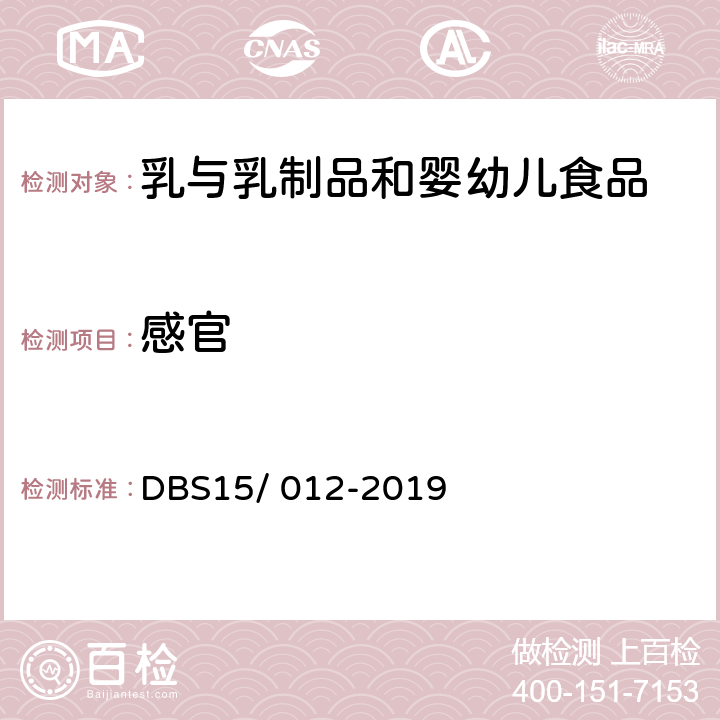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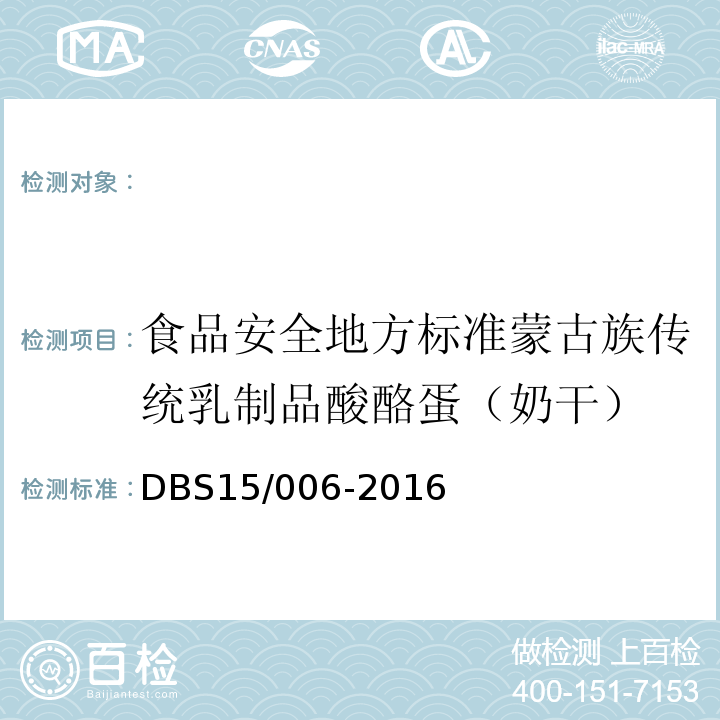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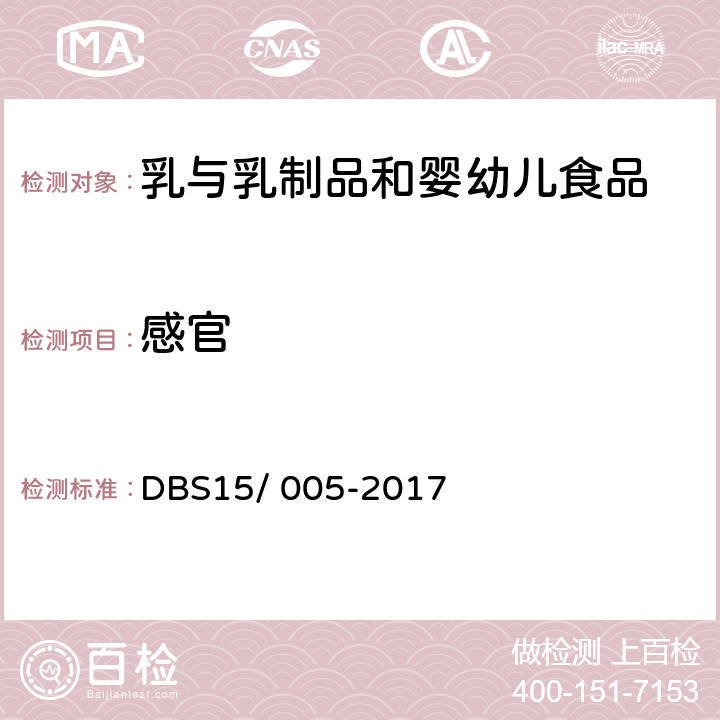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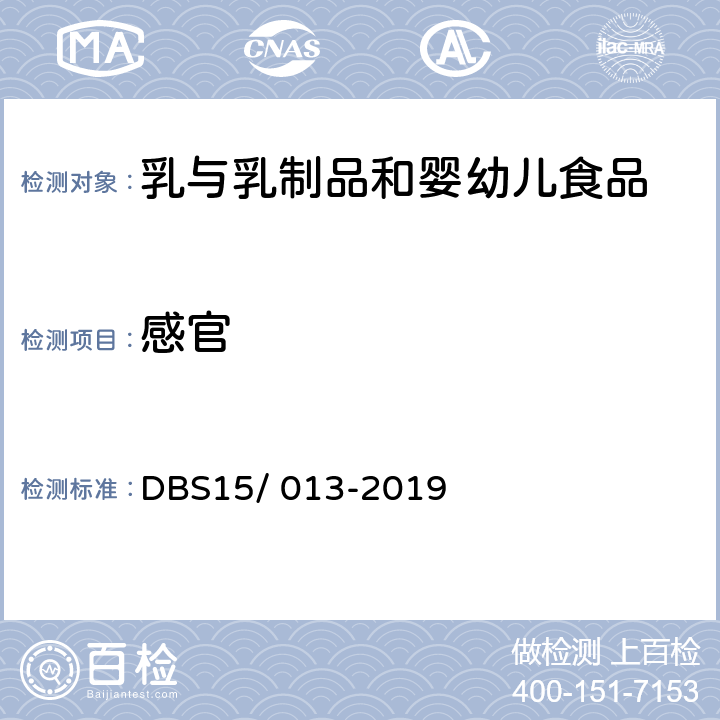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