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小孩。 石蒜科,大绒球 (Allium holandicum)。图片来自网络。
她坐在我对面,用小勺舀起一块冰淇淋,轻轻送入口里,慢慢品尝,微微地笑着。
她,一头齐耳短发,额前刘海用一枚简单的黑发夹,悠悠地划出一个好看的弧形,别在头顶上方,露出一张恬静、白皙的圆脸,仅在两腮处有天然的绯红,有种白里透红的感觉。她个头不高,也不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套,露出里面细花衬衣的领口。她总是微微地笑着,听别人讲话,很少插话。要是听到有趣的笑话,还会像一个羞涩的女孩子一样,用手捂住嘴巴想使劲忍着不敢笑出声来,生怕遭人讨厌。事实上,她牙齿和短发一样长得很整齐,白白的一排,露出来很好看。
她*大的优点就是见人就笑。哪怕主人下班回来,尝到她做的饭菜有些不合胃口,埋汰油盐放多了,她也只是抿着嘴,微微地笑着,*多就是自嘲般地稍微辩解两句。更多的时候,她就像家里的一只猫,安静乖巧,在收拾干净家里的卫生后,会拿起针线活,坐在阳台一角,为主人家纳鞋底,做布鞋。
是的,她是一个有主人的佣人,是一个花甲有余还在别人家做事的保姆。她,有夫有儿,也有家。可是他们离她的生活都太遥远了。她的丈夫,自她和他结婚后,稍有不顺,就会满嘴喷着酒气,无端地骂她、打她,一直到她离家出来做保姆才结束了这样的生活。几年前,两个儿子都长大娶妻生子,独立门户了,他们不需要她了,连刚出生的孙子都不要她带。幸好,她朴实善良,手脚勤快,动作麻利,凭着这份本领,她离开农村的家,到城里照顾别人家的孙子。
这一走,就是20多年,从不惑之年到花甲之际。年纪大了,很多家政公司都不敢聘用她了。然而,她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家就在抚仙湖畔,但是那里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张床。因为儿子们分家后,她和大儿子住,结果与儿媳妇不好相处,就再也没有了来往。小儿子有了分家的抚养协议,承担着养育她老伴的责任,也不愿意自己的妈妈回来一起住。安居乐业的儿子们,除了盖房子时需要她回家拿出在别人屋檐下挣来的辛苦钱外,到如今,也不想她的存款,想当然地不愿意履行他们赡养父母的责任。
图2:三色冰淇淋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我也静静地坐在她对面,并没有问她这些让人烦心的事情。我只是想在她回抚仙湖畔前,在这个她曾经做过10多年保姆的城市,像照顾一位长辈一样,带她来尝尝这些平日只能在电视里看得到的自助美食。我和她对坐着,中间是一个白色的小方桌。我面前摆放的是我喜欢的一杯咖啡和一块抹茶蛋糕。她取食的自然是百吃不厌的五谷杂粮,不过,多了一份香滑爽口的三色冰淇淋。我没想到一个老太太会喜欢吃冰淇淋。当我拿来一份请她尝尝时,我担心她会觉得凉,对胃不好。然而,她竟然像一个小姑娘似的喜欢上了冰淇淋,吃的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吃完,自己又去取了一些过来,说是就像以前在农村收获麦子时,口渴之际在村口小卖部吃到的冰砖。味道单纯的冰砖怎能和添加过上百种成分的冰淇淋相比呢?只不过是舌尖上的一种记忆复苏罢了。我依旧对她笑笑,没有多言,静静地看她开心吃冰淇淋的样子。尽管年纪大了,她却满头黑发,没有一丝白发,唯有脖子处的皱纹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看着她无声的用餐姿势,我敢肯定她以前在家做农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至少吃面条喝汤时,哧溜溜的声音是有的。因为她在家时,家里家外,地里田地都是她的活儿,农闲时也一样到建筑工地上和男人们一块儿挑水泥拌砂浆,如此繁重的体力活儿怎能顾得了细嚼慢咽的吃相呢?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江南水乡码头处,一头是做生意的大户人家,吃住体面,另一头就是靠帮人挑货提东西的挑夫,食宿简陋。那些挑夫蹲在家门口捧着一个海碗吃饭时,常看到他们用筷子飞快地扒拉着碗里的萝卜白菜,划到嘴里,尚未来得及咀嚼,就立刻被吞咽至肚里了。他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像干了**重体力活的挑夫一样,吃得如此酣畅淋漓、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美味都在挑夫们的碗里。
自然,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我也体验过干**农活后,饿的肚子咕咕叫的感觉;也曾看到过村子里端着海碗,哧溜溜吃得山响的壮劳力们。我自己也曾迫不及待地有声有色地填饱着瘪瘪的肚皮。只不过,我的吃饭哧溜声是小时候在妈妈一遍又一遍耐心的提醒下,并随着阅读面的拓宽而逐渐消失的。妈妈常说:“男人吃饭如虎,女人吃饭如数”。这句话既押韵又有趣,我听一遍就记住了。再者,书上也说,吃相斯文是女孩特有的美德。
那么,眼前这位衣着干净,吃相斯文的老太太又与我有何关系?我为什么要带她到这样一个闹市中的自助餐厅呢?君不知,我们吃完,起身要走时,她竟然倍觉惋惜地说:“一个人就要这么多钱啊!太贵了,自己买菜做饭够一家人吃好几天了。”我也只是笑笑不语。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我家小女上幼儿园前,请她过来帮忙带过孩子。小女入园后,她就去别人家帮忙了。偶尔,她也会打个电话来问候或者不打招呼就径直过来看我们,尽管时常因为我们出差不在家而吃闭门羹。她很勤快,来到我们家,总会主动地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模有样。她的到来,自然是倍受我们欢迎的。不过,我也承担不起养她的责任。听完她的故事,我只是陷入更深的沉默,再想不出别的好办法。
尽管她手脚勤快,不偷懒,不拿别人东西,养成了一种天然的家政职业素养,然而,她身份证显示她的年纪大了,该回家去养老了。可是,一个人飘摇在外20多年,就是每年春节主人给她的7天假期,她也不知该如何打发。因为她没有家可回,即使回到抚仙湖畔,她也常常跑到那些过年时缺少人手的小吃店里,帮忙洗菜,洗碗的,渡过那鞭炮声声除旧岁的新春佳节。当然,她很要强,也不愿受亲戚朋友邀请而去别人家团聚。她觉得即使再亲的亲戚,再好的朋友,那也是别人的家,不是自己的。
人,会老,还会老去。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只是迟早而已。我的父母就是早早地老去的那一类人。当父母相继老去时,才发现哪怕自己已经为人父母,可依旧难以面对失去父母的现状,不可避免地成为孤儿。而父母健在时,他们常常说起的那个故事又是多么令人羡慕。说的是,一个70岁的老头坐在家门口哭,路人关切地问为什么?他老泪婆娑,抹着眼泪,倍觉委屈地说:我爸爸打我!倘若,自己这把年纪,也依旧有父母责备两句,那也是一种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这就让人觉得古人的话语多么精辟而深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我也曾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曾依偎在父母跟前,信誓旦旦地说,等长大了,一定要给父母买糖吃,每天买一碗米线吃,还会开飞机带父母环游世界。可是,这些儿时的誓言早就随风,轻飘飘地飞走了,找不到一丝痕迹。
眼前,走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太太,她也到了儿孙绕膝、颐享天年之际。然而,她的儿孙却不愿往她身边靠拢,更不愿意谈到赡养。说到回抚仙湖后,要暂时借住在侄子家时,她无奈地叹口气说:“你说,我这么多年辛苦做保姆又有什么意思呢?两个儿子现在连钱都不向我要了。我要回去再接着帮人干活又有什么用呢?”忽然,我被她的话给怔住了。是啊,人的一生辛苦奔波忙碌为什么呢?为儿为女,也白搭:儿孙自有儿孙福呗。那么,人活着为了什么呢?这简单而又深奥的哲学问题竟然也开始困扰着这位目不识丁的老太太。
我看着她,回想起她吃冰淇淋的样子,一小口,一小口,微微地笑着。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和妈妈一块吃饭的情形。从地里忙碌**回来的妈妈,先放下镰刀锄头等农具,洗洗脸和梳梳头,稍事整理一下,就到厨房做饭去了。倘若在收获麦子的四月,她经常做的一道菜就是白菜豆腐汤。豆腐一定是那种煎得金黄喷香的臭豆腐,白菜一定是那种包得很紧密的卷心菜,很脆、很嫩、也很甜。当母女俩静静地坐在桌前,微微地笑着,轻声慢语地吃饭时,家里很安静,没有一丝声响。院子里那一丛玫瑰花开得正好,每个枝头都是盛开得如紫红色金绒布般发光的花朵,香气扑鼻,还能听到蜜蜂在花丛中的“嗡嗡”声。是啊,我多么希望,此刻身边的她就是我那失散多年的妈妈呀!
端午前夕,怀念我远去的妈妈。她的出生与离去都是在粽叶飘香的农历五月。



 1stGB/T 28948-2012 商用车辆 前端牵引装置 现行
1stGB/T 28948-2012 商用车辆 前端牵引装置 现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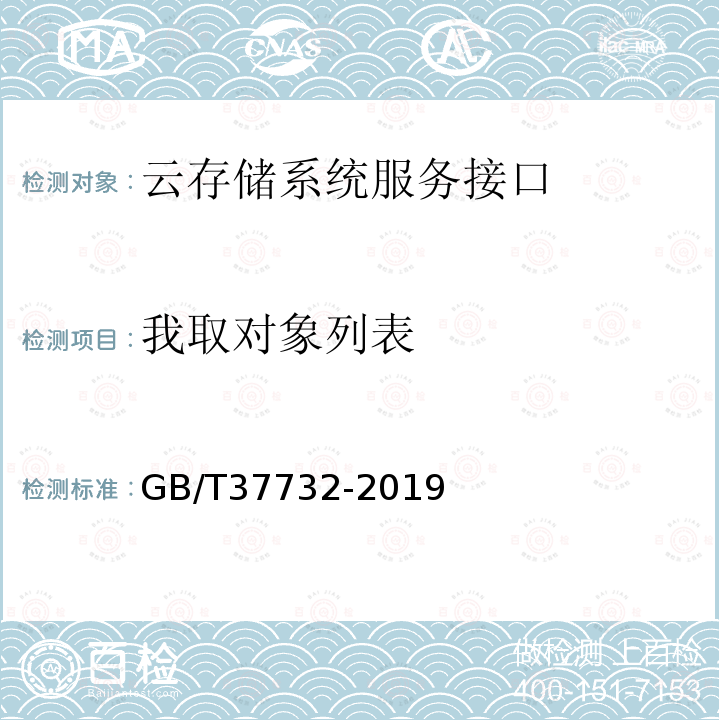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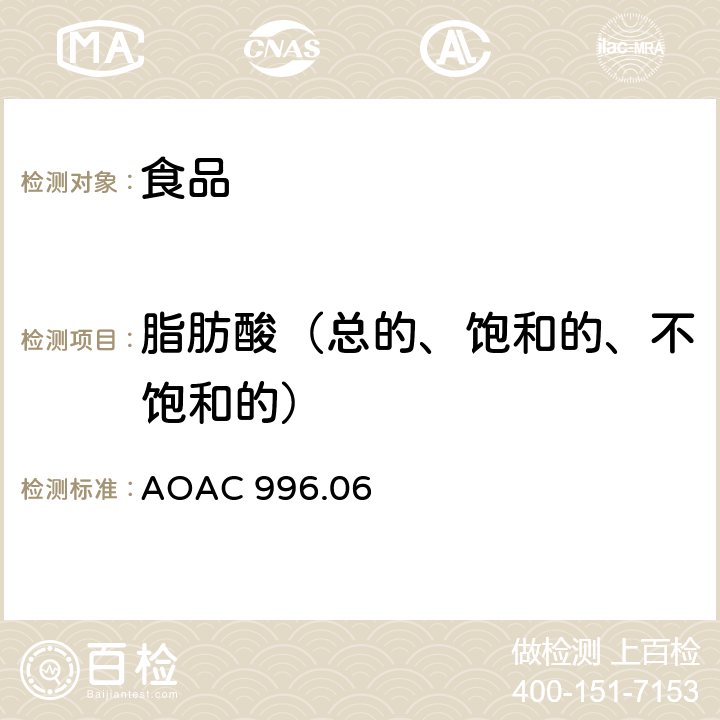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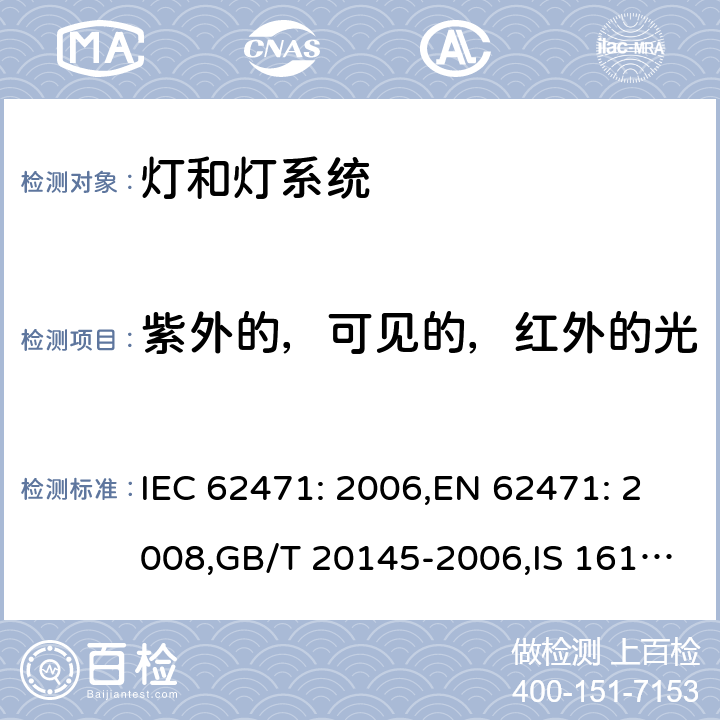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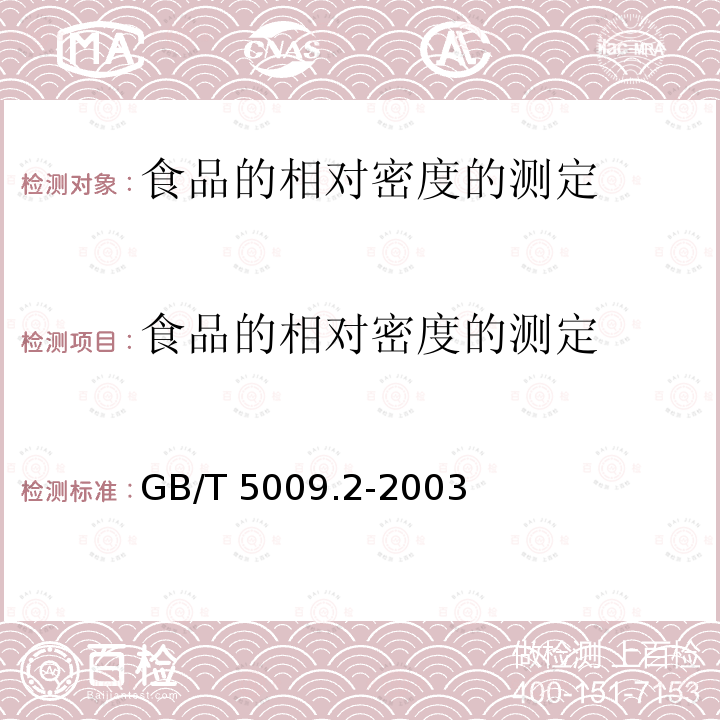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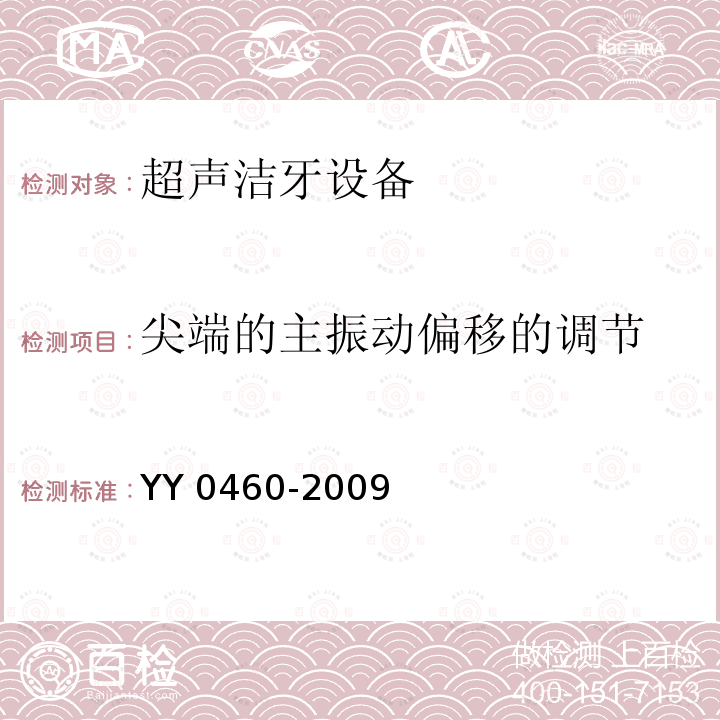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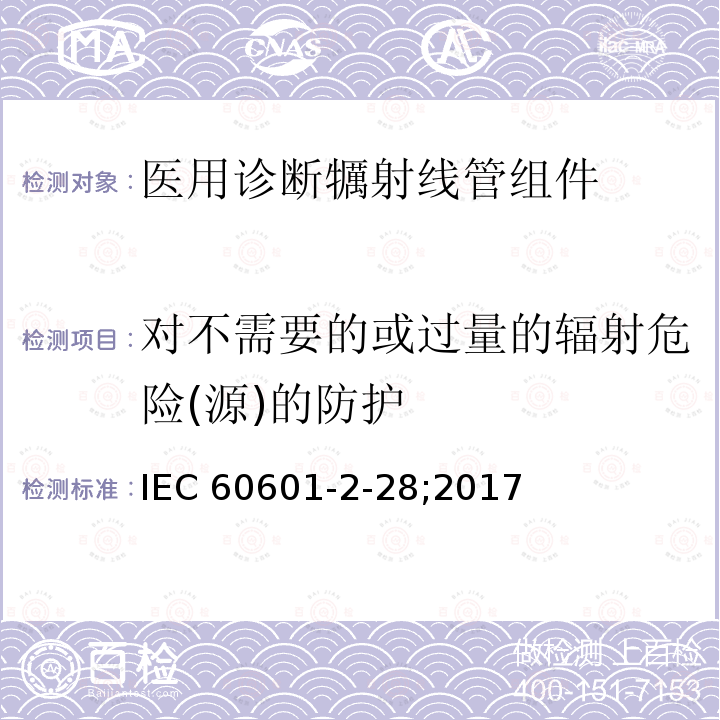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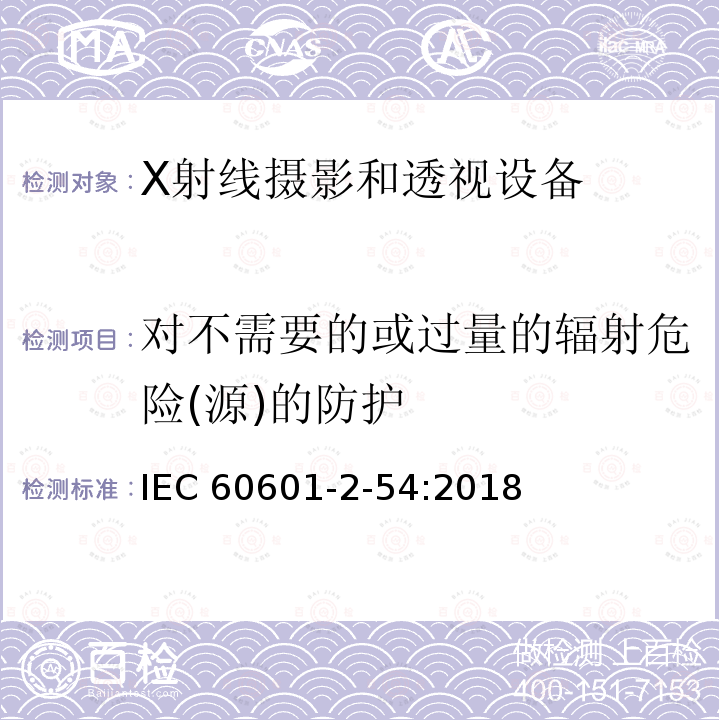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