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姚小鸥先生
小鸥先生:
一大早我女儿把你的一篇博文转发到了我的手机上。读过后我掉了泪。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这些年来身体又不好,本不宜再任由感情泛滥,但我怎么也止不住,一把又一把的老泪夺眶而出。
由你的这篇文章,那已经尘封三十八年之久的往事再一次浮现在眼前:它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鲜活,又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充满了血泪和痛苦,让人不忍直视。
那时,我刚满三十岁,正处于人生的*底层,在生死存亡线上进行着徒劳而绝望的挣扎。自从1968年高中毕业(我实为高中一年级,但也在那年“被毕业”)回到自己残破贫穷的农村老家后,十几年中,我先后从事过小学民办教师、公社通讯报道员和县广播站临时工等工作。收入菲薄,难以维生。三个两岁到七岁的孩子嗷嗷待哺,时有冻馁之虞。工作收入低不说,还很不稳定,时刻面临“失业”的可能。事实上,就在那一年,我*后的那份在临清县广播站打工的临时工作,由于受其单位中派性矛盾及人事纠葛波及,有一拨人正在背地里策划把我“清退”,逐回农村老家(真正的“清退”发生在第二年,即1980年,但出乎那些人意料又使其颇为尴尬的是,就在他们宣布开除我之际,我手里其实已握有一所大学录取我为研究生的通知书——当然,这些已都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谈)。
就是在这时候,我们人生中一个难得的机遇出现了:中国的高考在此前一年全面恢复。也是我那时太过年少气盛、偏执狂狷,对自己的实力自信满满。我竟轻易地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而直接选择了报考硕士研究生。也多亏了当时国家政策宽松,允许我一个高中生可以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那一年,我选择的报考对象,就是发生了我们“故事”的“那个学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导师是该校**学者庄维石先生。
这以后所发生的故事,就和你大文中所讲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那年,和你一样,我也同样收到了“那个学校”的不被录取通知书,上面并附有各科成绩。让我惊诧的是,我心里还有些底数的外语(俄语)成绩仅只20多分。照我自己的估算,怎么也得在50分以上(因为这门课是有一定预判基础的)。带着这个疑问,我设法搭车去了济南,到“那个学校”负责招生的相关部门进行探问。一个工作人员听了我的申诉,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告诉我:你试卷*后一道译文题(也是分值*高的一题)被弄丢了,现在已经找了回来,加起来这门课的成绩在50分以上,达到了录取要求。但学校招收研究生工作已经结束,都已经向上级部门报备,结局(即不被录取)不可能改变了(大意如此)。
可怜当年我是那样的无知,那样的呆傻。我这个乡下来的土老冒,何曾见识过大学这么**又神圣的地方,又何曾和在大学这样高层次地方工作的人对面讲过话。在我眼目中,人家说的话句句都是圣旨,说什么我都是既相信又服从。因此,尽管我心中万分委屈,结果也只有半是无奈又半是情愿地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
当天,我还去了庄维石先生家。
庄先生很热情,听了我的来意后,立即拿出一张纸给我看,说我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成绩都不错,已在拟录取的三个考生之列。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说到这个专业已被取消招生资格后,他的语调立即变得十分高亢激越起来:“本来我并不想招收研究生,是他们非让我招;我要招收的学生他们又不批准(原话如此。你大文中的引述稍有出入)”。当时,我不知道庄先生此处所说的“他们”是谁?而“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手段和伎俩粗暴地谋杀了一门专业的招生权利,从而也谋杀了那在万难境遇中挣扎求生,希冀进取发展的无辜学子们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以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我也完全没有考查求证出这些情况的能力。
*后,庄先生表示,他此后不会再招研究生了,如果我真的有志于此,他愿意把我的情况介绍给山东大学的袁世硕先生。后来,据说庄先生终其一生,真的没有再招收过硕士研究生。而我由于个人原因,第二年改报了聊城师范学院薛绥之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并蒙恩师录取,从而失去了向袁世硕先生问学的机缘,也永远地改变了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初衷。每念及此,真是感慨良多!
对我而言,几十年前,当我强自吞咽下万般的悲苦和委屈,独自默默地离开“那个学校”研究生科大门的一霎那,这个故事就已经结束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完全把它深深地埋藏到了心底深处,从此不再对任何人提起。因此,当然,话又说回来,那时,我既使想说又能向谁诉说呢?说了之后又会得到些什么呢?况且,我那时还年轻,还要重理我的生活,我总不能把那种苦涩经常含在喉间去自我品味吧!更久一些时候之后,似乎连我自己也都淡漠了,淡漠了它的存在。
然而,真所谓世事难料。万万没有想到,在茫茫人海中,我们本来天各一方,素不相识的两个人,竟在垂暮之年*度偶然地邂逅了。你作为京城一家知名大学的知名学者,竟鬼使神差地受聘于我们这个地方性大学的工作,并又*度偶然地从意外场合听到了我的一些讯息。一切都充满了“意外”,一切都是“奇迹”!
于是,便有了那一次在我办公室的我们之间的**次会面,也即你文中所说的“重要时刻”。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在我们身上曾发生过的那个故事又得以继续演绎并匡正、增补进了不少新的内容。如果说那个“故事”在之前我们两人心中都还有些混沌模糊的话,那么,有了那次会面,一切都变得清晰明郎起来。我们用各自的经历、各自的所知所感,互印互证了当年那一谋杀和罪恶的确切存在。特别是你文中引录的那位“匿名”先生在百检网上的“留言”,更以其客观、冷静地角度,为这桩“历史公案”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在此,我对那位“匿名”先生表示万分感谢!
诚然,在不相干的人们看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件尘封往事及其此后的揭露过程,真的只是一个还算有点意思的“故事”,但对我们当事者而言,可真的一点都不好玩。那种年代、那种世相、那种嘴脸,其间的切肤之痛,真是一言难尽。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吧。
小鸥先生,我一生心仪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但那件事永远地剥夺了我的这个权利,也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事业和人生轨迹。这是我至今都引以为憾的。
不过,既然事已至此,该放下的总还是要放下。况且,如今事实真相既已水落石出,横亘在我们心中几十年的疑云都已消散。我们总算到老来落了个心里明白。我们都已年届七旬,须发苍然,来日无多,何必再让那种历史的负累相伴自己的余生呢!就是对“那个学校”及其策划并实施了那番谋害的人们,我也已觉得无话可说。就让他们为自己的一时之计得逞而继续地弹冠相庆吧(如果他们还在世)。
和庄维石先生我仅谋一面,此后再也没能见到他,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在我脑海里鲜活如生。听说他前些年已离世,愿他老人家的灵魂在天国里永远得到安息!
如有可能,我也愿意结识事件中的另一位受害者——武润婷女士。不知道她是否仍在山东大学。我想,将来我们三个人如有机会聚会一次,可能会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你每到学校来时,希望都设法告诉我一下。
写得很多了,就此打住,不再冒渎清览。
顺祝
文安!
宋益乔 2017.12.1---2日



 1stYD/T 1251.2-2013 路由协议一致性测试方法 开放最短路径优先协议(OSPF)
1stYD/T 1251.2-2013 路由协议一致性测试方法 开放最短路径优先协议(OSP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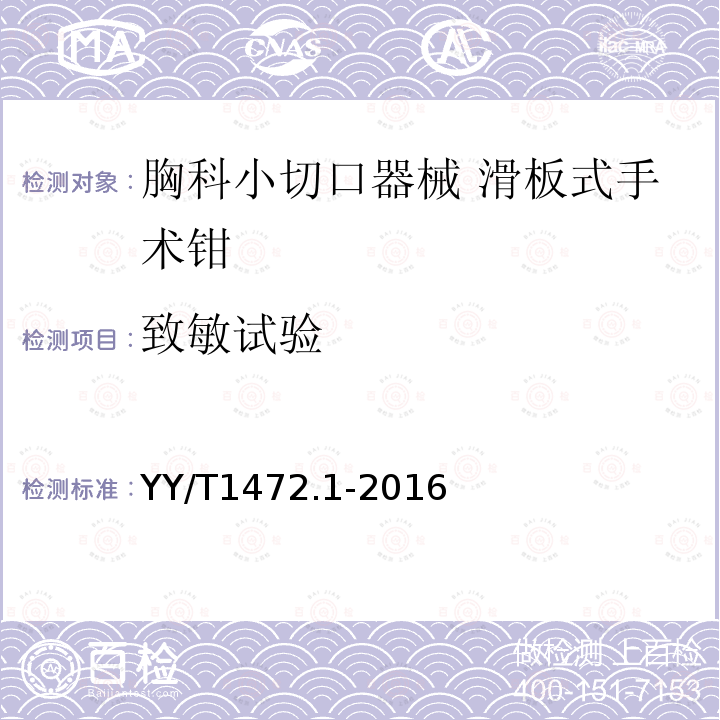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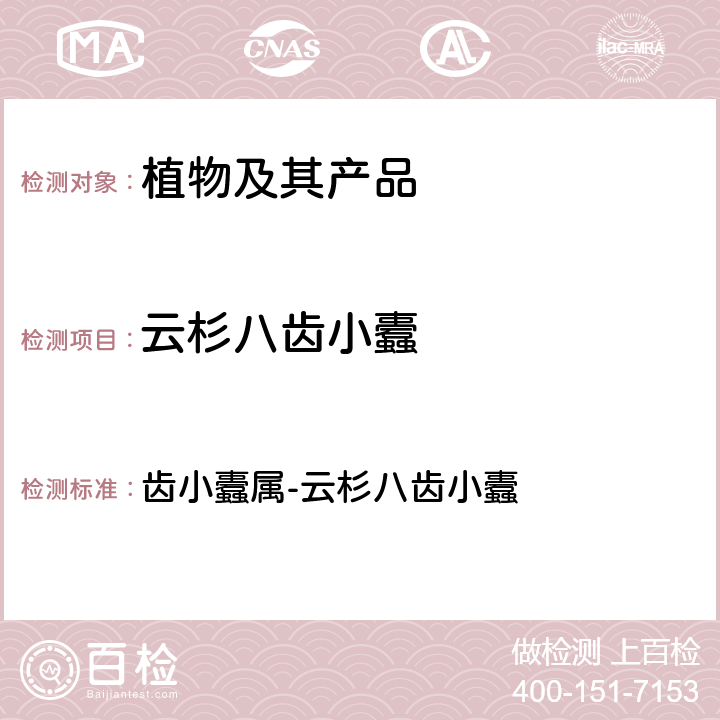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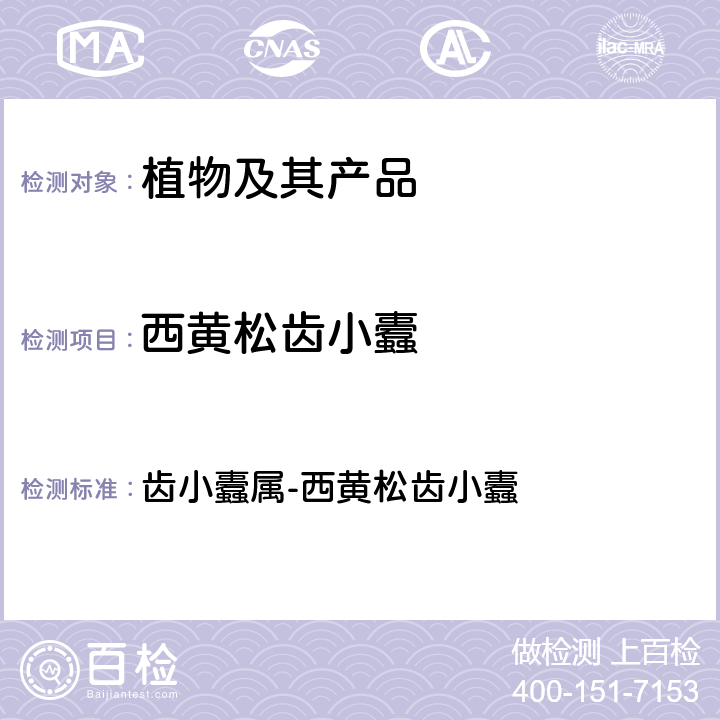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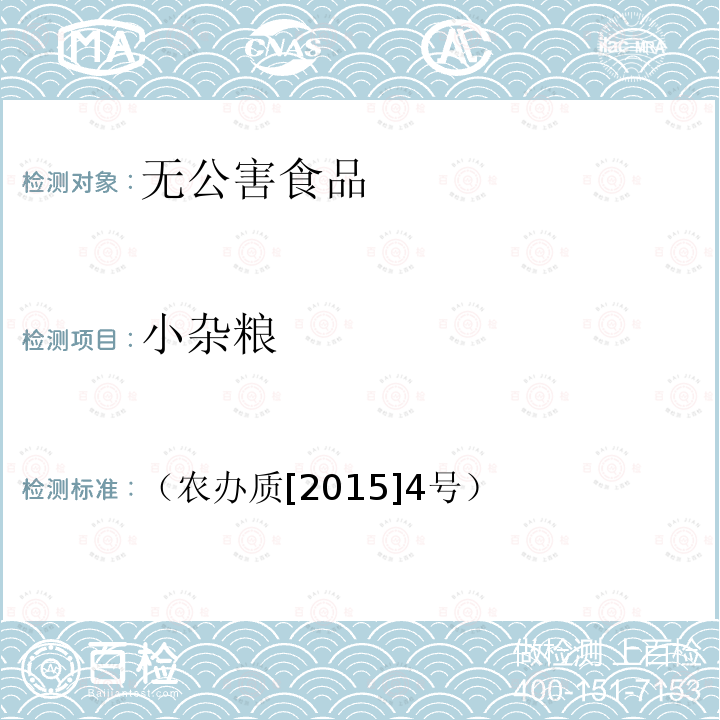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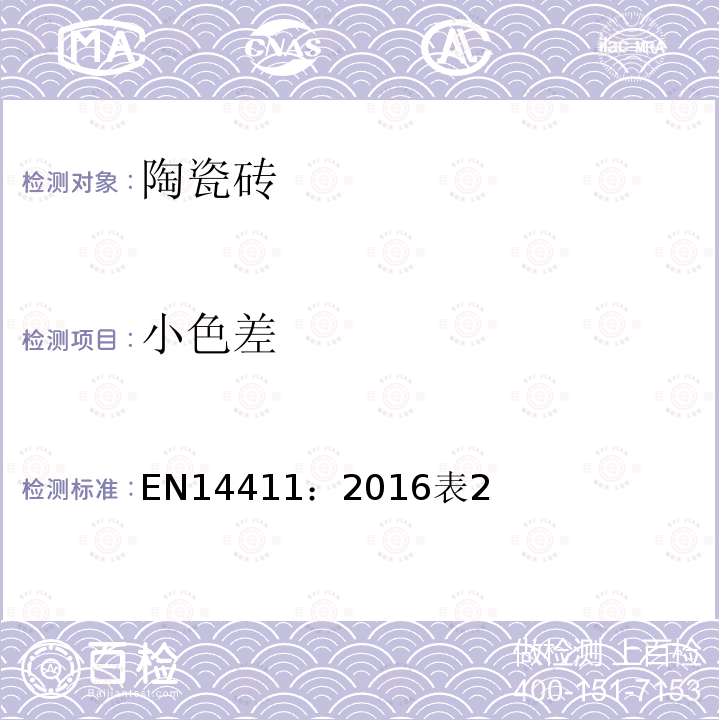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